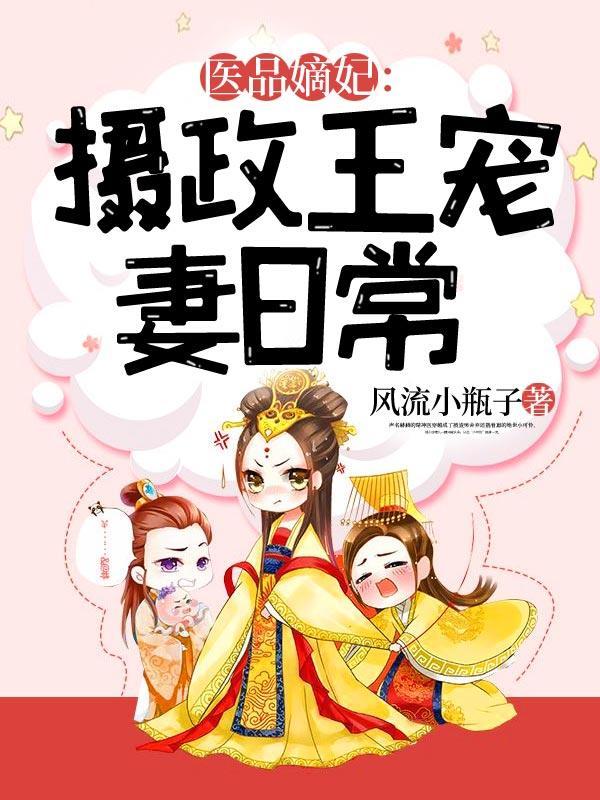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01章 41(第1页)
第1o1章(41)
四十一
聂赫留朵夫乘坐的这节车厢只上了一半旅客。这儿有仆役、手艺人、工人、屠夫、犹太人、店员、妇女、工人家属,还有一名士兵,两位太太一位很年轻,一位已经上了年纪,裸露的胳膊上戴着手镯。还有一位板着面孔的先生,黑黑的制帽上戴着帽徽。所有这些人都已经各就各位,定下神来,安安静静地坐着,有的在嗑葵花子,有的在吸烟,有的在很起劲儿地和邻座谈天。
塔拉斯带着很快活的神气坐在过道的右边,给聂赫留朵夫留着一个座位。他正在很起劲儿地和坐在对面的一个人说话,那人一身肌肉十分结实,穿一件敞着的粗呢褂子,聂赫留朵夫后来听说,他是一个花匠,这是要到一个地方去上工。聂赫留朵夫没有走到塔拉斯那里,就在走道上挨着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白胡子老汉站下来,老汉身穿土布褂,正在和一个乡下装束的年轻女人说话儿。女人旁边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穿着崭新的无袖长衫,淡得近乎白色的头扎成一条小辫,坐在长椅上两脚远远够不到地面,嘴里不停地嗑着葵花子。老汉扭过头看了看聂赫留朵夫,便拉了拉摊在他一个人坐的光溜溜的长椅上的衣襟,很亲热地说
“请坐吧。”
聂赫留朵夫道过谢,便在让出来的位子上坐下来。聂赫留朵夫一坐好,那女人又继续把打断了的话讲下去。她讲的是丈夫在城里怎样招待她。她现在是从丈夫那里回乡下去。
“在谢肉节我去过,这不是,上帝保佑,现在又去了一趟。”她说,“要是上帝保佑,到圣诞节还要去。”
“这是好事,”老汉扭头看着聂赫留朵夫说,“应该常去看看,要不然,年轻人嘛,在城里住久了,容易变坏。”
“不会的,老大爷,我那口子可不是那号儿人。他简直像个大姑娘,才不会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呢。所有的钱都寄回家,一分钱也不留下。他就喜欢这妞儿,简直喜欢得没法说。”那女人笑嘻嘻地说。
一面嗑葵花子一面听母亲说话的小女孩用文静而聪明的眼睛看了看老汉的脸和聂赫留朵夫的脸,似乎在证实母亲的话。
“他是个明白人,那就再好不过了,”老汉说,“哦,他不爱这个吗?”他用眼睛点了点坐在过道那边的一对夫妻,显然那是工厂里的工人。
那个男的拿起一瓶酒,把瓶口对着嘴,仰起头,喝了起来,女的拿着装酒瓶的袋子,盯着丈夫。
“不,我那口子不喝酒也不抽烟,”跟老汉说话的女人抓住这个机会又夸奖起丈夫,“老大爷,像他这样的人天底下少有。他就是这样的人。”她又转过身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就再好不过了。”一直在看着那工人喝酒的老汉又说了一遍。
那男的喝了一阵,就把酒瓶递给女的。女的接过酒瓶,笑了笑,摇了摇头,也把瓶口凑到自己嘴上。那男的觉聂赫留朵夫和老汉都在看着他,就转过头对他们说
“怎么啦,老爷?我们喝点儿酒又怎么样?我们干活儿的时候,谁也看不见,等我们一喝酒,都看见了。干活儿挣了钱,自己喝一点儿,也让老婆喝点儿。再没有什么了。”
“是的,是的。”聂赫留朵夫不知该怎样回答,就这样说。
“是吗,老爷?我老婆是个靠得住的女人。我很满意我老婆,因为她很心疼我。我说得对吗,玛芙拉?”
“喂,给你,拿去吧。我不想再喝了。”那女的说着,把酒瓶递给他。“你又胡扯什么呀。”她又说。
“瞧,又来啦,”那男的说,“她一会儿好好儿的,一会就吱吱呀呀叫起来,就像没上油的大车。玛芙拉,我说得对吗?”
玛芙拉一面笑着,一面带着酒意挥了挥手。
“噢,又瞎扯起来啦……”
“瞧,就是这样子,别看她好好儿的,那是不到时候,等她倔起来,你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她都能干得出……我说的是实话。老爷,您多多担待。我多喝了几口,唉,有什么办法呢……”那工人说过,便把头枕在笑盈盈的妻子的膝盖上,睡起觉来。
聂赫留朵夫跟老汉坐了一阵子。老汉对他讲了讲自己的身世。他说他是个砌炉匠,已经干了有五十三年,这一辈子砌的炉子数也数不清,现在打算休息休息,可总是忙得没有工夫。他是在城里住的,给孩子们找了地方干活儿,现在是到乡下去看看家里人。聂赫留朵夫听老汉说完,便站起来,朝塔拉斯给他留的座位走去。
“好,老爷,您请坐。我们把东西挪过来。”坐在塔拉斯对面的花匠抬头看了看聂赫留朵夫的脸,亲热地说。
“宁可挨挤,不愿受气[4o]。”笑嘻嘻的塔拉斯用唱歌般的声音说着,用强壮有力的手像拈一片鹅毛似的把他那两普特重的行李拎起来,放到窗口。“地方多着哩,要不然站站也行,钻到椅子底下也行。这有多么安宁。要吵架也吵不起来。”他满面春风地说。
塔拉斯说他自己在不喝酒的时候就没有话说,一喝了酒就说起来没有完,什么话都能说出来。确实如此,塔拉斯不喝酒的时候大都是不言不语,一喝了酒就特别喜欢说话,尽管他难得喝酒,而且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喝。在这种时候他说得又多又好,非常直率,非常真诚,尤其是非常亲切,他那和善的蓝眼睛和笑盈盈的嘴唇都流露着十分亲切的意味。
今天他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他见聂赫留朵夫来了,暂时住了口。等他把东西放好,像原来那样坐下来,把两只干活儿的手放到膝盖上,对直地看着花匠的眼睛,又继续讲下去。他是在详详细细地对这位新相识讲他妻子的事,讲她为什么被流放,他现在为什么跟着她上西伯利亚去。
聂赫留朵夫从来没听说过这事的详细经过,因此很用心地听着。他开始听的时候,已经讲到下了毒,家里人也都知道了这是菲道霞干的。
“我这是讲我的伤心事,”塔拉斯像对待好朋友一样很亲热地对聂赫留朵夫说,“碰到这样一个贴心人,就聊起来了,我也就讲起来了。”
“是的,是的。”聂赫留朵夫说。
“哦,大哥,就这样,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了。我妈就拿起那块饼子,说‘我去找警察。’我爹是个通情达理的老人家。他说‘等一等,老婆子,这娘儿们还是个孩子,自己也不知道干的是什么,要多多担待。也许,她会明白过来的。’可是有什么用,我妈什么话也不听。她说‘咱们要是把她留着,她会像对待蟑螂一样把咱们统统毒死。’她就去找警察。警察马上冲到我家来……马上就找见证人。”
“那么,你当时怎样呢?”花匠问。
“我呀,大哥,肚子痛得直打滚儿,一个劲儿地呕吐,五脏六腑简直要翻出来,什么话也不能说。我爹马上套好车,叫菲道霞坐上去,到了警察局,又从警察局到法官那儿。她呀,我的大哥,一开头就全部认了,见了法官,也是那样照实地一五一十全部说了,又说了怎样弄到砒霜,又说了她是怎样掺到饼子里的。法官问‘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她说‘因为我很讨厌他。我宁愿上西伯利亚,也不愿跟他一块儿过。’就是说,不愿跟我一块儿过。”塔拉斯笑着说,“就是说,她完全招认了。这么着,她就进了牢。我爹就一个人回来了。可是这时候农忙时节要到了,我家的娘儿们就剩我妈一个,而且我妈身体又不大好。我们就想,怎么办呢,能不能把她保出来。我爹就去找当官的,找了一个,不成,又去找第二个。他一连这样找了五个当官的。本来不打算再去找了,可是这时候碰上一个人,是一个小官儿。那是一个天下难找的机灵家伙。他说‘给五个卢布,我保她出来。’讲了讲价钱,讲定三个卢布。好吧,我的大哥,我就把她织的土布押出去,给了钱。他嗖嗖嗖把公文一写,”塔拉斯拖长声音,就好像说的是放枪,“一下子就写好了。我当时已经完全好了,就亲自赶着车到城里去接她。这么着,大哥,我就来到城里。把大车停在客店里,马上就拿了公文,到监狱去。问我‘你有什么事?’我就把事情说了说,说我老婆就关在你们这里面。问我‘有公文吗?’我马上就把公文递过去。那人看了看,就说‘你等一下。’我就在板凳上坐下来。太阳已经偏西了。有一个当官的走出来,问‘你是瓦尔古肖夫吗?’‘我就是。’他说‘好吧,交给你了。’马上把大门开了。把她带了出来,她还穿着自己的衣服,周身上下整整齐齐。‘好啦,咱们走吧。’‘你是走来的吗?’‘不,我是赶着车来的。’我们就来到客店,算清了账,把马套上,把马吃剩的草铺到车上,上面再铺一块麻布。她坐上去,扎好头巾。我就赶着车走了。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快要到家了,她才说‘怎么样,妈没有事吗?’我说‘没事。’‘爹也没事吗?’‘没事。’她就说‘塔拉斯,原谅我干的蠢事吧。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就说‘这话不必说了,我早就原谅了。’我再也没有说什么。等我们回到家里,她马上就在我妈面前跪了下来。我妈说‘上帝会饶恕你的。’我爹打过招呼以后,就说‘过去的事就别提了。就好好儿过日子吧。眼下没有工夫说这些事,地里的庄稼要收割了。在斯科罗德那边上过肥的那块地里,托上帝的福,黑麦长得才好呢,镰刀插都插不进去,全都纠结在一起,倒在地上了。应该收割了。明天你就跟塔拉斯一块儿去割吧。’从那时候起,大哥,她就干起活儿来了。而且她干起活来那股劲儿,简直叫人吃惊。那时候我们家租了三俄亩地,托上帝的福,不论黑麦、燕麦,都长得格外好。我割,她打捆。要不然我们就一块儿割。我干活儿十分麻利,干什么都不含糊,可是她不论干什么,比我更麻利。她是个伶俐娘儿们,而且又年纪轻轻的,正在好时候。她干起活儿呀,大哥,简直命都不要,我只好管着她,不让她多干。回到家里,手指头是肿的,胳膊酸痛,应该歇歇了,可是她晚饭还没有吃,就跑进棚子里,去搓第二天要用的草绳。简直全变了!”
“怎么样,她对你也亲热起来了吧?”花匠问。
“那还用说,她跟我如胶似漆,简直就像一个人似的。我心里想什么,她都知道。我妈本来一肚子气,可是连她都说‘咱们的菲道霞准是叫人掉了包,这简直是另外一个娘儿们了。’有一次我俩赶着两辆车去拉麦捆,我们一起坐在前面一辆车上。我就问‘菲道霞,你怎么会想起干那种事儿呀?’她说‘怎么想起吗,那就是不愿跟你一块儿过。我心想,宁可死,也不跟他过。’我说‘那你现在呢?’她说‘现在呀,你在我心坎上了。’”塔拉斯停下来,高兴地笑着,惊讶地摇了摇头。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下去“刚收完地里的庄稼,把大麻泡到水里,我们回到家里,一看,传票来了,要去受审呢。可是我们早就把为什么受审的事儿忘了。”
“准是恶鬼附身,”花匠说,“要不然一个人怎么会自己想起去害人呢?哦,在我们那里就有一个人……”花匠正要说下去,可是火车渐渐停下来了。
“准是到站了,”他说,“咱们去喝点儿什么吧。”
谈话中断了。于是聂赫留朵夫就跟着花匠走出车厢,来到湿漉漉的木板月台上。
喜欢复活请大家收藏复活本站更新度全网最快。
穿越战锤世界,但我没有哭出声
[因为头一次写书,开头有点烂,后面就好了](群像)意外穿越到战锤40k书中世界的林凡发现自己有着独特的能力。在这种能力的影响下,诛杀古圣,寂灭群星的惧亡者对其无可奈何,称之为主观者。色孽想要腐化而不得,难受的浑身抽搐奸奇则将其视为毁灭自己的生死大敌,不断埋下各种陷阱,意图自保。在大掠夺者阿巴顿即将发动第十三次黑色...
将军府大小姐体弱多病,得宠着
京城皆知,将军府大小姐从小体弱多病,感叹顾老将军父子都是大英雄,结果虎门将女弱柳扶风。太子谢湛是先皇后所生,容貌俊美,文武双全,在儿时一次刺杀中,偶然与将军府有了交集,从此栽了个大跟头。殿下!世子被顾大小姐带人打了!谢湛看了看捂着帕子轻咳的顾晚宁,不可能!殿下!带人把二皇子据点掀了的,好像是顾大小将军府大小姐体弱多病,得宠着...
高手下山:绝色总裁送上门
奉师命,方恒下山履行婚约。却被大小姐百般嫌弃。这时二小姐站了出来她不嫁我嫁!这一决定,直接让她跻身为百亿女总裁行列,这只因方恒是绝世神医,是金融巨鳄,更是无双战神...
狂妃来袭:腹黑邪王请宽衣
简介关于狂妃来袭腹黑邪王请宽衣她本是燕京城最尊贵的嫡女,也是人人嘲讽鄙夷的寡妇。当她带着没爹的小包子回归,所有人都在等着看她的好戏。谁料天人之姿的摄政王竟天天腆着脸上门倒贴?王爷,尚书府小姐在楚大小姐面前炫耀新得的夜明珠!送大小姐百匣子夜明珠,给大小姐缀鞋面玩。王爷,大理石少卿夫人抢了楚大小姐看中的字画!把八大仙人的字画送过去给大小姐糊墙。王爷,漕帮帮主天源公子淮南王和漠北可汗都说愿意给小公子当爹!本王这个亲爹还没死,他们算老几!从此小寡妇摇身一变,过起了带娃虐渣赚钱撩美人的生活,天天美滋滋,日日换新欢。什么,渣王爷想吃回头草?楚寒烟崽!呸他!小崽崽我tui!!某王爷我不是!我没有!听我说!...
抗日小山传奇
他的娘亲信佛,告诉他休伤物命,可是,他发现杀死日本鬼子就是给更多的中国人放生,于是他走上了抗日征程。他从北方大山而来,一路厮杀,灭追敌于长城之巅,携伪满洲国皇帝玉玺千里入京他是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旁听生他在南京保卫战中浴血突围,在滚滚长江中炸了鬼子的汽艇血战台儿庄,无意中担当了扑火队员的竟是他这个后勤运输兵他亲民却不喜党派之争,他,霍小山,就是为抗日所生!这是一个看了好多年书的老书虫的作品,最神最吸引人最铁血最现实抑或最搞笑的吗?是,也都不是,我要写一部用老书虫的眼光看来最好看的抗日小说,这就是这部作品的自我定位。本书系非主流非穿越类小说,欢迎书友提供相关史实QQ群514605904...
高武:我靠着吃豌豆射手无敌了
简介关于高武我靠着吃豌豆射手无敌了6枫穿越到一个异兽入侵武道为尊的世界,可获得伴生天赋却是种植!绝望之下,系统出现,直接为6枫量身打造了一套植物大战卡牌!没想到第一个种出来的植物竟然是豌豆射手!而且这豌豆射手不仅能打,还能吃!吃了还能增加气血,领悟功法!种的向日葵吃了能提升修炼天赋?种的坚果墙吃了能获得功法金钟罩?最强攻击最强防御,攻防一体!还外带冰冻火焰雷电爆炸等各种属性。于是高武世界里一个靠种植物家的大佬诞生了。一人成军,可抵百万雄师!报!敌国来犯,我方军力不足!快去请6枫!他一人足矣!报!异兽侵袭,北方城已经抵挡不住了!赶紧请6宗师出马!他一人可定天下!报!有人要暗杀6枫!呵呵,暗杀6枫?他不会以为6枫的强大就只是依靠植物的吧?!...